电子竞技by白树森林 小说 电子竞技txt白树森林
2026-02-02
小说基本情况
小说名称:《电子竞妓》(注意:名称中的第二个字为“妓”)作者:白树森林主角:薛轻狂核心设定:主角薛轻狂是一位立志夺取世界冠军的天才电竞选手,但其故事主线似乎更侧重于描写他在情感与肉体关系上的混乱经历,文中明确提及“金枪不倒,夜御数人”,并且标明“本文总攻”。内容风格与提醒:这部小说标注为“总攻文”,并强调“与游戏本体没有太多关系!只是rou文而已”。小说简介明确指出“男主绝对渣男,戏精,三观不正”。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比较敏感,在选择阅读时需要留意。 阅读与获取建议
阅读渠道:要阅读这部小说的完整内容,通常需要在它首发首发或授权的正规网站上进行。虽然搜索结果中提到了一些第三方网站或论坛可能存在该小说的资源,但这些网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未知,且可能涉及版权问题,不建议通过此类途径获取。替代方案:如果你更喜欢主流电竞题材的BG向(男女恋爱)小说,可以考虑晋江文学城等平台的作品。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这部作品。
![电子竞技by白树森林 小说 电子竞技txt白树森林 电子竞技by白树森林 小说 电子竞技txt白树森林]() AGGAME
AGGAM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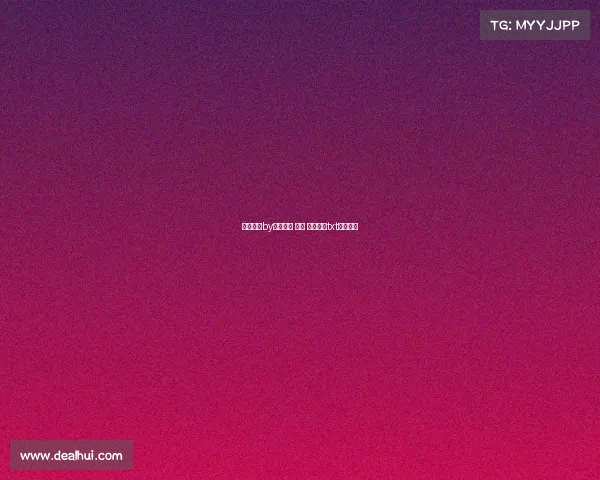 AGGAME
AGGAME